|
在我自己的思想成長過程中,受到的來自中國作家的影響很有限;在這有限的幾個人中,翻譯家董樂山先生是一個。不是被他本人的作品,而是被他的翻譯作品所影響。幾本有限的關於極權社會的英文著作,如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庫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動物農場》等,竟然都是董樂山先生翻譯的。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讀《一九八四》時所受到的震撼至今難忘,而由那本書所產生的對極權社會的理解和痛恨,遠超過我本人由於在共產社會的生活體驗而帶來的對獨裁專制的認識。所以對翻譯介紹這些作品的人,一直心存感激,更有一份和譯者的無言的共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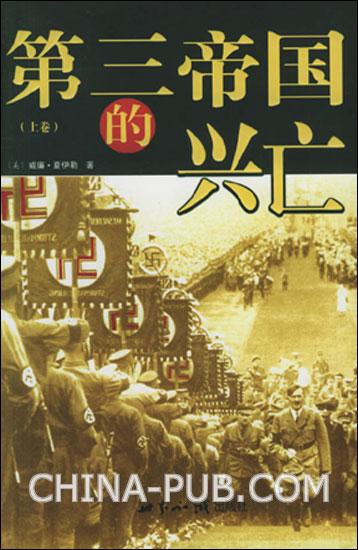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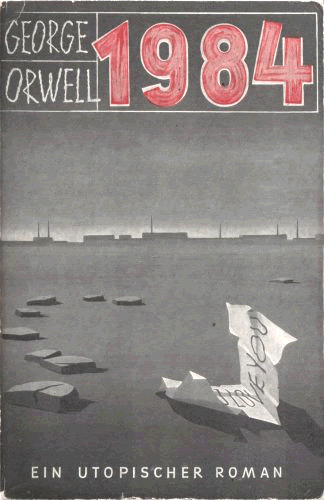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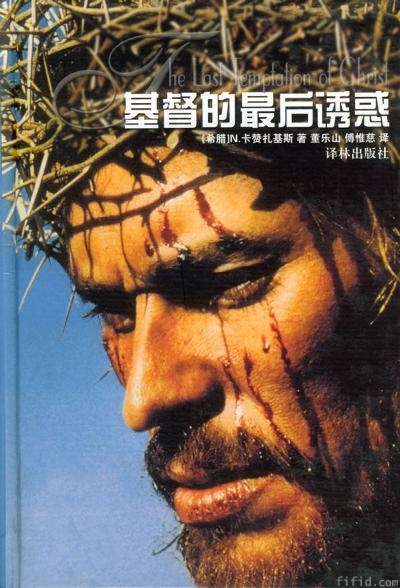

● 中國著名翻譯家董樂山漫畫像(下)及他翻譯的幾本名著。
為弟弟沒有原諒他而傷心
今年一月十六日是董樂山先生去世十周年。他的哥哥董鼎山先生在上期《開放》撰文,再次提到他和弟弟因思想差異而產生的爭執和隔閡,而且董樂山到死都沒有原諒董鼎山的「為中共張目」(董鼎山引董樂山語) 。董鼎山為弟弟沒有原諒他而傷心,同時耿耿於懷地再次指責董樂山是「在極權社會中成長的知識人士,往往養成一種看事物很極端的態度」,他認為這種態度是「非黑即白」,然後給扣「文革陋習」的帽子。
董鼎山自己「幫中共講話」(董樂山語),除了董樂山會把他「厲聲大罵一頓」之外,別人也並沒和他過不去(那種左傾的東西,當今親共海龜寫得比董鼎山更多);可是他自己卻一再撰文批評別人反共、親美的觀點是「非黑即白」,並給扣文革帽子。就此,我曾在○三年寫了題為「在大是大非面前沒有灰色地帶」的文章,指出「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功夫,抵銷著董樂山用血和淚所做的努力。怎麼應該是董樂山給董鼎山道歉?完全應該是董鼎山給董樂山道歉才對!」
美國也有一個類似的故事
五年過去,董鼎山不僅依舊相當左傾,仍對董樂山對他的憤怒不能理解,更對我的批評無法釋懷。不過他在上期《開放》文中貶義地指我「對中共嫉惡如仇,猶如樂山」倒讓我感覺很褒獎。本無意再撰文,但由於董鼎山再次提到董樂山的不原諒他,使我聯想到美國著名哲學家、小說家安.蘭德(Ayn Rand)對她妹妹的絕不原諒。因尚未看到中文世界有人提及這一段,所以覺得值得一敘。
安.蘭德在二十一歲(一九二六年)時離開蘇聯來到美國,從此用英文寫作,成為二十世紀最影響美國人思維的、最受大眾歡迎的小說家(不是「之一」)。她的《巨人聳聳肩》(Atlas Shrugged)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全美最大讀書俱樂部一九九一年聯合舉辦的「最影響你人生的一本書」的問卷中,排名僅次於《聖經》。她對極權世界對人類的踐踏,痛恨到沒有一毫米可原諒的餘地。由於她對西方左派的毫不妥協的、黑白分明的痛斥(稱西方左派是為虎作倀的爪牙),所以從來都被以親共、親左、反美為壓倒多數的西方知識份子們嚴重排斥。這也是中國人直到近年才聽說安.蘭德這個名字的原因。
安•蘭德離開蘇聯後,前十多年還和家人保持通信聯繫,二戰後則音信斷絕;後來聽說家人全部在戰爭中被炸死。事實上她最疼愛的、和她最趣味相投的小妹妹諾拉還活著。七十年代中期,諾拉在一本美國雜誌關於當代名人的介紹中發現了姐姐安。她馬上給姐姐寫了一封信,寄到美國的雜誌社,請他們幫助轉寄。安在接到編輯部打來的電話、說她的小妹妹還活著並寄了信來的時候,幾度喜極而泣。她隨後設法把四十七年沒見面的妹妹(和妹夫)接到了紐約,在自己住的樓裡給他們租了帶高級傢俱的公寓,並準備在新澤西俄國人社區給他們買房子,讓他們永遠留在美國。
安蘭德為何跟重聚的妹妹反目
但姐妹相見後立刻發生了衝突。倍受共產洗腦的諾拉認為所有外人,包括安請的司機、傭人、朋友等,都是監視她們的間諜。她雖然也覺得蘇聯缺少自由,但同時又認為,「自由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呢?我也不是政治活動家。」而且諾拉很快就開始抱怨美國,認為紐約髒亂差,還不斷說列寧格勒有多好。安一開始還努力試圖給她解釋,但很快瞭解了諾拉是不可救藥。尤其是會英文的諾拉竟然對姐姐那些對無數美國人起到了巨大影響的書毫無閱讀的興趣,這也讓安很傷心失望。姐妹倆關係迅速惡化到幾乎無法對話。結果六個星期後,諾拉夫婦就決定回到蘇聯。從此姐妹倆再沒聯繫。而且後來一提起諾拉,安就十分憤怒。
在這個故事裡,最具諷刺意義的是,諾拉跟誰抱怨美國,也不應該跟那個比全世界任何人都更熱烈推崇美國價值的安•蘭德抱怨;跟誰讚美蘇聯,也不應該跟那個和極權世界不共戴天,不僅對蘇聯,對整個俄國都絕不說一句好話的安.蘭德去讚美。董鼎山董樂山的故事,也具類似諷刺:海外文人盡可撰文親共左傾,卻最不應該是那個對專制厭惡至極、中譯了最多反極權著作的董樂山的哥哥。
安和諾拉姐妹倆的反目,雖然和董鼎山、樂山的反目相反,是住在自由世界的姐姐不原諒住在極權世界卻為蘇聯辯護而不珍惜美國的妹妹,但從根本上來講是同樣的,那就是:痛恨極權社會的一方,不能原諒對獨裁社會的任何辯護;對專制政黨,更沒有餘地。原則高於血緣和親情。沒有對極權社會的深惡痛絕,就不會有對自由像呵護生命一般的珍惜和不顧一切的追求。
夏志清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相當一批享受自由世界的華人,都拐彎抹角地為專制的存在辯護。在董鼎山那一輩人裡,親左、親共是相當普遍,他不是異數。但異數絕對有。我○三年那篇批評董鼎山的文章發表後不久,在一個會議上見到夏志清先生,他馬上對我說,「你罵董鼎山的文章寫得好,寫得好;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只是夏志清的口頭禪而已)。事實上,像夏志清這種根本沒受過共產蹂躪的人,能認清專制本性,堅定反共,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和董鼎山同樣是在年輕的時候就來到美國,同樣是沒有親身體驗過共產專制的暴虐,但夏志清的始終如一的堅定、堅決、義無反顧的反共,一直令我十二分敬佩。夏志清和董鼎山都住在紐約,年齡也相仿(夏志清一九二一年出生,董鼎山一九二二年),兩位的同樣高壽和思維活躍,倒是同等令人佩服。但根本不同的是,凡是和反共有關的會議,夏志清是每請必到,而董鼎山則從不見蹤影。當然,或許大家都知道他的立場,也不請他。
其實,安•蘭德的妹妹,只要認真地讀讀自己姐姐的作品,就應該會瞭解為什麼極權社會不可被容忍,為什麼那麼多美國人推崇自己的姐姐。同樣,董樂山的哥哥,只要認真讀讀自己弟弟的翻譯作品,他也應該會明白,為什麼反共是沒有任何餘地的,為什麼會有像我一樣的中國人感激董樂山的努力。
我周圍的親友,不乏如蘭德姐妹和董家兄弟這種原本親密無間的血肉之情,卻因在自由和極權兩個完全不同社會的生活,而反目絕情。故事講起來容易,但這背後有多少傷心、失落、多少遺憾、多少無法挽回的不了情!董鼎山先生可能比我體會更深。他那篇文章的題目「至愛兄弟不了情」頗令我感覺他那份傷感。比他年輕的弟弟卻早在十年前就故去了。這難道和專制沒有關係嗎?盼董鼎山先生保重,好好享受你的自由世界。無論自由世界有多少人為專制辯護,為獨裁添磚加瓦,我都為他們能生活在自由世界而替他們感到慶幸。
自由是多麼美好,但我從不敢忘記那些仍在專制夢魘中的兄弟。
二○○九年一月十二日於美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