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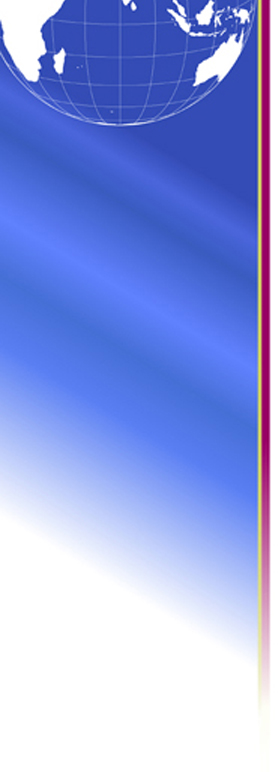 |
是是非非的周揚 ● 周揚文革前是貫徹毛路線的左王,文藝界一根打人的棍子,但歷經文革劫難後沉痛反省由左返右,因此對周揚的評說亦各有不同。 李輝曾編過一本《是是非非說周揚》,也就是不少人評說周揚的集子。從集名上就可以看出周揚乃是非人物。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央視十套文藝頻道「大家」欄目採訪著名導演謝鐵驪,謝先生回憶中仍提起一九六三年文化部領導集體審查影片《早春二月》,文化部長茅盾等人一致鼓掌,惟周揚嗅覺特敏,當即指出該片帶有明顯的修正主義傾向,走入陀思妥也夫斯基「自我完善自我犧牲」的人性論泥淖。後來,影片《早春二月》與《北國江南》一起遭到公開批判,一時間全國有數百篇文章猛烈開火。當然,《早春二月》現已躋身新中國十大經典影片之列,乃是為謝鐵驪先生帶來最多榮譽的平生傑作。 周揚長子是「黑大」內定自由化人物 因為上述關係,大學畢業二十餘年來,我一直十分關心周揚,十分關心涉及周揚的文章。最近,本人從香港開放雜誌上讀到一篇寫於一九九二年的《懷念周揚》,作者是一九五○年代名噪一時的河北青年女作家劉真。劉真乃山東夏津縣流浪兒,一九三九年被八路軍收留,一九四三年入黨,一九五二年入學東北魯迅藝術學院,一九五三年再入中央文學講習所,畢業後先入武漢作協,再調河北作協,現旅居澳洲。(按:見本期讀者來信) 周揚確實根據上級精神整過丁玲、胡風、馮雪峰、艾青 ...... 一九五○年代,丁玲曾說:「他把魯迅的人都打光了。」 但對當時的青年作家劉真來說,周揚卻是她的伯樂。周揚不僅早在延安就發現了她大哥晉駝的小說才氣,而且還發現了她的文學才華。一九五六年因周揚的推薦,她的兩篇小說(《春大姐》、《我和小榮》)分別被長影和北影拍成故事片。劉真頓時聲譽鵲起,一九五六年全國青年作家代表會,進了主席團,與老舍一同在懷仁堂舞臺上主持大會,連周恩來都坐在邊上。 劉真談周揚文革前右的一面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批示說作家不接觸工農兵,做官當老爺,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周揚頂抗這一批示,立刻要求每一作家彙報下鄉下廠的時間,用以向毛澤東說明作家們並非脫離工農兵。一九八九年七月周揚去世,劉真出席八寶山追悼會,發現雖然各界唁客不少,但沒有人哭他,情緒輕鬆。劉真感慨:「多年來,他作了那麼多次長篇大報告,發表了那麼多文章,死後竟沒有一篇文章悼念他,肯定他一生的辛勞,似乎他的名字不叫《周揚》,叫﹃沒法說﹄。」 左王鄧力群不滿周揚的作風 當然,劉真與周揚接觸有限,只是一個小小的側面,不可能說明周揚「左」與「右」這樣的大問題。各人的感覺也很不一致,如丁玲因自己的徹底平反受到陸定一與周揚的阻撓,認為周揚晚年到處道歉,多向那些間接受害者,而未向自己、陳企霞、艾青這些直接受害者道歉。因此,丁玲對周揚晚年的「自左返右」很不以為然。不過,劉真的文章作為周揚的一個側面,至少可以說明文革前的周揚並不完全「左」到了家,多少還有所保留,而且能意識到「無產階級專政弄不好比資產階級專政還厲害」,這也說明文革後他由左返右,實在有著相應的歷史根源與思想基礎。 人確實是十分複雜多面的,尤其涉染政壇的大人物,公心私慾交錯糾纏,很難從一個角度觀察到全部行藏,前後行為也不可能符合邏輯的一貫性。但是,劉真這篇《懷念周揚》還是再次說明:誰做過的好事,人們是不會忘記的。對大人物來說,則是歷史是不會忘記的||成敗毀譽,賬還是會一筆筆算清楚的。 (一):《鄧立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 》,二○○五年印行,第一八七|一八九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