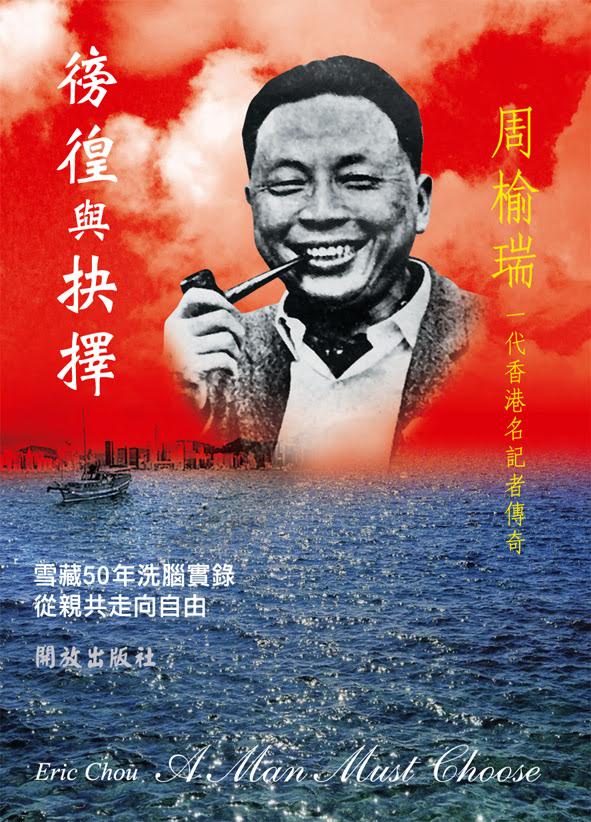
第十章
北京花園囚徒
當天晚上,我已入睡了,助理管獄員到我的獄室來把我叫醒。
「把你的東西收拾起來跟我走。」
我興奮極了,當我收拾東西的時候,手也開始發抖。他和一名衛兵把我帶到驗放室,那個斜眼審訊員和另外一名年青便裝人員已經在那裡不耐煩地踱來踱去。
我看見我的衣箱、手提箱和另外一件行李已放在地上。
那個斜眼共黨對我說:「趕快、你現在跟我們一起到北京去。我現在給你十分鐘時間來收拾行李,要快點!」
我呆住了,最少幾秒鐘後我才清醒過來。
他大聲說,「繼續收拾吧!我們要趕十一點三十分的班車,知道了嗎?」
到那時,我才知道我馬上便要離開這個監獄。可是,由於我向來不善於收拾行李,我的動作緩慢,而且笨拙。那個斜眼共黨徒不耐煩了,他叫那個便裝人員幫我的忙。
當我收拾妥當以後,他很嚴肅地對我說:「你的案件須由北京當局決定。所以,我們現在把你送到北京去。照規矩,一個囚犯在旅途上是要扣上手銬的。可是,為了你的面子,我們不想這樣做。我們相信你不會在火車上企圖逃走──事實上,你也逃不了的。不過,在我們到車站去以前,我還要明白地告訴你幾點:第一,你要絕對服從我們。第二,如果你在火車上碰到任何熟悉的人,你必須像陌生人一樣不加理會。第三,你要到洗手間的時候,必須先向我們其中一人報告。明白了吧?」
我點點頭,沒有出聲。
他們把我押離了監獄,我們三人同搭一輛黑色雪佛萊轎車,不到二十分鐘的工夫,我們已經到達了北站,那時已是十一點二十五分。還有五分鐘便要開車了,他們迅速地把我推上頭等車廂,並趕快把窗簾拉下來,車廂裡只有兩個臥鋪,那個審訊員命令我睡在上面的臥鋪,他們兩人便輪流睡在下鋪。
五分鐘後,火車開行,我幾乎立即睡著了。
當我於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火車已經在南京──浦口處渡過長江。我在南京很快活的住過和工作過,因此想到南京就使我難過。
看守我的人沒有跟我談話,也不願和我同桌吃飯。由於我的錢已退回給我,我便可以在每頓飯叫三樣菜。我這樣的揮霍金錢,他們自然不會看不到,可是他們沒有阻止我。
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四日的早晨,直達通車在北平的前門車站停下來。當其他乘客正在魚貫下車的時候,看守我的兩個人把我關在車廂裡,其中一個首先走下月臺。幾分鐘後,一輛救護車駛到月臺,它的出現使我相信,我將被送往醫院去。
然而當我一走進這車輛裡,我便發覺那是一輛偽裝的囚車。我靠著坐位的一邊,從小窗孔向外偷偷望了幾眼,看守我的人馬上喝止我。
一種無法形容的感覺直透我的心房,當那輛汽車開始加速前進的時候,我便閉上眼睛,沉緬於回憶中。二十二年前,我來到這裡進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唸書,渡過了三年的十分愉快的日子,直到中日戰爭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發為止。在那些日子裡,北平是中國文化的搖籃,吸收了和培養了來自中國各地的最傑出的學者、教授和作家。對於一個年青的學生來說,再沒有比能夠在北平的一間大學唸書更使他愉快的了。此外,「五四」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國發動第一次學生運動的紀念日,這一項運動,在其本身的意義上和影響上說來,都可與文藝復興媲美。
我以囚犯的身份再度來到北平,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我在大學生活時代,是以表現反國民黨情緒著稱,我甚至被認作共黨的同情者。可是現在,中共卻把我當作他們的敵人,甚至不給我以公平的公開審訊的機會。
當這輛「救護車」終於駛進北平市北城區某處的一個大院子時,我從沉思中醒過來。看守我的人帶我走下車去,領我走進一株大棗樹下的一個小房間。
我只消看一眼,便知道這是一間典型的北平房子。可是我自然不曾料到,北平的一間監獄會看起來好像一座普通的民房一樣而不漏痕跡。
當我在等待的時候,我在外衣口袋裡摸索餘下來的香煙,因為我預料在旅途中給我的吸煙特權,不久將會消失。我接連抽了所剩的三隻香煙。
這時候,一個操湖南口音而身材不高的人高視闊步地走過來,從上海一路看守我的兩個人以畢恭畢敬的態度把一封公函交給他,他迅速地過目,然後用一個手勢打發他們走了。
他轉問我說:「你要在這裡等待判決,我不需要告訴你這裡的規矩了。從今以後,你的編號是零四五四,你不許把你的名字和背景告訴任何人。」
他隨即掀鈴,一個年輕人走進來。
「帶他到A座第八號單人獄室去。」
這個年輕人向我招手,說:「這邊走。但我要你面對著牆壁的時候,你得立刻照辦。」
我跟著他走出這個小房間,走過大庭院,穿過一道門,走進另一個院子,這個院子比較小,樹木則較多。在遠處的盡頭有一座灰色的房子,這個年輕人把門打開,我於是走進一個很寬敞的大廳,那一定是所有獄室的樞鈕地帶,因為在每一邊都有一些門。
我還來不及思考建築物的設計,那個年輕人已經把其中的一道門打開來,帶我走進一條像地道般的甬路,要把我關進去的獄室就在甬路的末端,剛好與廁所為鄰。
我發現那獄室有兩個窗,一個對著地道,另一個對著寬大的花園,園裡滿是垂柳和松樹,獄室的面積約莫是十六呎乘十二呎,有一張木床靠著牆壁。我馬上感到我不必再睡在地板上,於是鬆了一口氣。令我大感驚奇的發現:我看見床上有兩張新的棉被。
跟上海的兩座監牢比較起來,這個監獄無疑是舒服些。獄室裡沒有特殊的限制,我可以隨意走動,坐著或者站在對著花園的窗子旁邊。正式的獄卒雖然態度不錯,但公安部派來的警衛確是令人討厭,他們每隔五分鐘便從窗孔窺我一次,以奇特的態度直瞪著我的臉,這使我緊張起來,心裡不安。
那兩個獄卒一肥一瘦,都是北平人,極有可能是中學畢業生。我在無意中知道了他們的教育程度。有一天,他們在我的窗下談著他們不久前參加過的某間大學的入學考試,其中一個渴望做醫生,另一個想攻讀土木工程。他們並且也都是學生的樣子。
快到五月底,我關進這個監牢後才第一次被傳訊。審訊室在這座監獄中老遠一個角落的一座新房子裡。
我走進去,覺得不勝詫異。以前在上海向我問起劉尊棋和柯家龍的那個北方人坐在一張長的紅色桌子後面,笑容可掬。
「你還記得我嗎?」
「當然記得,你到上海去審訊我。」
「抽一支煙吧,」他向我走過來,依然帶著微笑。「事實上我不是審訊你。我只是要你把關於你以前的兩個同事的資料供給我。你在這裡已經很久嗎?」
「二十二天了。」
「有什麼不滿嗎?」
「嗯,有的。在上海,我後來是吃小灶飯食。在這裡,他們再把大灶飯食給我吃。還有,我得不到任何讀物。」
「唔,這兩件事情都可以有辦法。現在,我需要你的幫忙。自從我們上次在上海談過之後,你有想過關於劉尊棋和柯家龍的補充資料嗎?」
「沒有,真的沒有。我自己的案件怎麼樣呢?我要等多久才有結論呢?」
「因為你已經來到這裡,那是不會太久的。同時,我會要他們給你好一點的飯食,自然也給你讀物。」
我對他表示感謝,然後被帶走了。
兩天後,我再被傳訊。這一回,我在另一個房間看到新的面孔,他是一個矮傢伙,穿著整潔的灰褐色毛絨「人民裝」。他的鬍子刮得很乾淨,一雙皮鞋在陽光照射下發亮。
他微笑說:「坐下來。」
凝視我幾秒鐘後,他問道:「他們有沒有給你小灶飯食呢?有沒有給些書你讀呢?」
我笑笑。「他們都答應過我。」
「我知道了。那是說他們的承諾還沒有依言兌現,我說得對不對?」
我再笑笑。
「這裡還有別的使你不高興的事情嗎?」
「嗯,我不喜歡這些黑色的衣服。」我指著我的囚衣。「這套衣服給我許多不愉快的感覺。」
「真的這樣壞嗎?」他縱身大笑。「你不會穿得很久了。噢,關於M你還有甚麼事情要說的嗎?」
「我已經把一切關於他的事情寫下來。」
「我也這樣想,可是,假如你還有一些要補充的話,為什麼不現在就在此地補充呢?」
「你說就在這裡?」
「噢,不,我是說當你回到你的房間裡突然想起要寫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不再提出問題,他開始同我談到我的小說和我在香港的生活方式。他好像對香港很熟識,但從他的四川口音看來,他不像是到過香港。
差不多過了一個小時,然後他才站起來,向我說:「我不久就會再看到你。」
我返回獄室,那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我坐在床上,聽到獄卒把別的獄室門打開,讓犯人走出去拿飯菜,可是永遠輪不到我。
飢餓和焦急交集,我站起來,準備透過窗孔一詢究竟。就在這個時候,我的監房的門給打開了,另一個獄卒拿著托盤走進來,托盤上放著兩盤熱氣騰騰的菜,一碗湯,和一盤白麵粉做的饅頭。
他對我說:「這是你的飯菜,要是饅頭不夠,我可以再拿些給你。」
我結結巴巴地說:「夠了,夠了,多謝你。」
甚至到現在,我依然記得那兩盤菜是核桃雞丁和紅燒排骨,湯裡有雞蛋和番茄。廚子顯然是個老手,兩樣和湯都達到菜館的水準。我可以聽到我自己貪婪地大聲咀嚼食物的聲音。
當獄卒再來收拾碗碟時,他帶來了我的灰色蘇格蘭厚呢西裝,兩件襯衣和幾條領帶。他說:「你現在可以換上你的衣服了。」
這些東西簡直像是屬於別人的。因為我的體重減輕了差不多六十磅,我馬上可以看出我的西裝和襯衣都不再合身了。
「我不想要這些衣服。此外,保留我的領帶和腰帶是違反規則的。」
「不要管規則。我們接到命令,要把這些衣服還給你,如果你高興,你也可以選擇另一套衣服。要是你不想穿,你還是可以把它留在你的房間裡。」
獄卒是個好人,我無意使他感到為難,於是我從他手中接過那些東西,堆在床上。這時,我的確不在乎穿著囚衣,雖然我向四川籍的審訊員提出過這個問題。我寧願看起來像一個普通的囚犯。
第二天早上,身材矮小的湖南人來到我的獄室,告訴我他們准許我選擇我的讀物。他的說話使我想起了我衣箱裡的英文書,我要求取得這些書。
他表示同意,說:「好吧,你可以拿到你的英文書。不過。你要把書名用正楷寫好,以便我們查核。」
照我記憶所及,我的衣箱裡有里頓·史特拉齊的《維多利亞時代名人傳》、海明威的《太陽上昇》和韋氏大學辭典。我把這些書名用正楷字寫好。他拿了書單倒轉過來看,然後問道:「你還要別的書嗎?」
這個問題使我想起我向C.S.借來的那部《當代美國詩集》。我把這本書加進單子裡。
他們至少費力一小時才把這些書拿來給我,那這些書放在身旁,我覺得好像百萬富翁那麼富有。有了好的食物,心愛的作家,和一張相當舒服的床,獄中的日子過得很快。
每天早上,值班的獄卒帶我到鄰江的花園,在垂柳和松樹下散步,當我在太陽下沿著小徑漫步時。我有時竟會充滿著詩意。
我無須像在上海的兩座監獄那樣,要自己動手洗衣服,獄卒每個星期來兩次,把我的汙穢的衣服拿去。我猜想,他把衣服交給勞動改造的犯人去洗滌。若是天氣晴朗,乾淨的衣服在幾小時內就給拿回來。那真是迅速之至。
在這些空閒的時間裡,我時常想到我的未來。但每逢我憂慮的時候,「聽天由命」這句中國老話總是給我解圍。我自然極想念我太太,我母親和我的孩子,可是我最後總能以一些愉快的想法來安慰自己。
有時我甚至告訴自己,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不斷拿這個監牢同上海的那兩個監牢來比較,覺得這個監牢舒服多了。此外,失去了自由將近四年之後,我好像已經習慣了監獄的生活。「自由」這個字,對我來說,已經成為模糊不清,失去了它的意義。我冷誚地想:既然中共區實際上是一個大監獄,住在真正的監獄裡,又有何妨呢?在外面,你可能被拘捕;可是在監獄裡,至少你不必有這個憂慮。我經常依賴我的直覺,現在,直覺告訴我,我將會在北平獲釋。我把《維多利亞時代名人傳》讀過一遍又一遍,我的目的在於改進我的英文文體。在我看來,用英文來撰寫我的經歷的機會正在越來越近了。自然我有時咀咒自己沉溺於一廂情願的想法和愚弄自己。不過,在那種環境下,我是很難把一廂情願的想法和希望區分開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