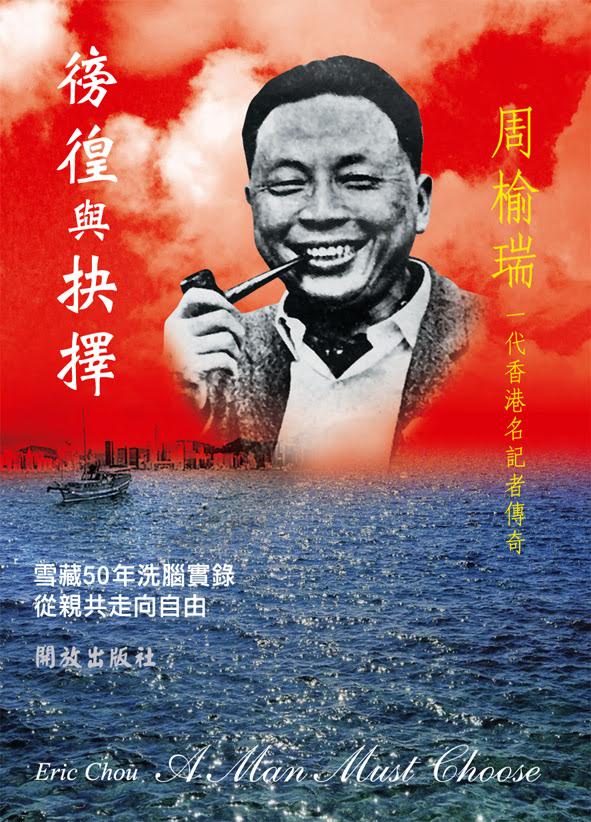
第十二章 受命國際統戰
我在北平,有兩次得到觀察共黨怎樣去組織群眾的機會。他們的效能和手段都很高明。
快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底,印尼總統蘇加諾飛抵北平從事官式訪問。在他到達的前夕,約在晚上八點鐘,一個看來像普通家庭主婦的中年婦人來看周老頭,她只是站在院子裡,說了幾句簡單扼要的話。
「蘇加諾總統明天下午兩點鐘左右來到北平,為了表示我們對他的熱情,政府已經決定動員一百萬北平的居民表示盛大的歡迎。在這間屋子裡,你們有四個人,這條胡同的街坊小組希望你們當中派出兩個人,在下午兩點鐘以前到這條胡同的東面出口附近的西單大街。在蘇加諾總統經過這條大街之前,你們不要走開。」
周老頭向她保證支持她的要求,她隨即向他道謝,然後走了。這個老頭兒談話的興緻很好,他告訴我,這個女人是街坊小組的一員,逢著這些場合,街坊小組便負責動員居民。他同時建議,我可以在次日下午到大街去看看。
到那個時候,老張和周老頭陪同我到西單大街去,這條大街距離我住的屋子只有五十碼之遙。兩旁的人行道塞滿了人──老年人,家庭主婦,學生和小孩。人群分五六層排列著,手裡拿著鮮花和旗幟。他們閒談、歡笑和東張西望。我們看不到武裝的士兵,但是有幾個警察沿著人行道踱步。
約莫在下午二時三十分,站在老遠那邊的人群開始歡呼,靠近我們的那些人也跟著歡呼。我掉過頭來向西望,見到三輛敞篷的汽車正緩慢地駛過大街。在第一輛汽車裡,北平衛戍司令楊成武站在一個印尼將軍的身旁,他們全幅戎裝,像所有的職業軍一樣,面露嚴肅的表情。
毛澤東和蘇加諾並肩站在第二輛車裡,那是一輛流線型的黑色派克牌篷車,在秋天的太陽照耀下閃閃生光。歡呼的聲音越來越響,震耳欲聾,毛露出微笑。有些人衝進大街上,把花擲到那輛派克牌汽車上,他們距離毛和蘇加諾只有五呎,衛兵並沒有攔阻他們。
周恩來和印尼外長在最後的第三輛車。他們都面帶微笑,揮動著手,可是歡呼聲已沒有那麼熱烈了。
當我回想起來,我的腦海裡一直想著這些歡迎的場面,整個局面是在事前經過很好的安排,但我猜想,在蘇加諾的心目中,一定認為是出於自動的表現。
我在十月一日第二次經歷了這種場面,那是中共的「國慶日」。趙安排我在那天以公安部來賓的身份去看五十萬人大遊行,也許這是對我的再教育計劃一部分。彼時「公安部」大樓在天安門廣場,對面就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和周恩來等首腦人物的檢閱臺。
毛澤東和蘇加諾在八時二十五分出現,隨後是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和其他高級共黨人員。如雷般的歡呼和喝彩聲立即從廣場的每一個角落響起來。毛裂嘴而笑,向群眾揮手,群眾也作熱烈的反應。
在八時三十分,北平「市長」彭真以簡短的致詞來宣佈慶祝儀式開始。鳴禮炮二十三響後,跟著遊行便開始了。遊行的人包括了小孩、婦人、工人、農夫、工程師、教授、學生和軍人,他們排列成十六個縱隊前進。
坦克車、裝甲車和大炮隆隆而過,同時有十二架噴射機飛過廣場上空,吸引著群眾的稱讚,高呼口號,搖動著手中的紅旗。
我必須承認,群眾所表現的熱情和歡樂曾經打動了我,我甚至有一種不可言宣的感覺,使我講不出話來。
共黨動員群眾的手法的確是驚人的,文昭曾經告訴我,五十萬人列隊走過受禮臺將需要五個小時,當最後一個人走過廣場的時候,那正是下午一時三十分。「十一」遊行這樣就結束了。
那天晚上,老張燒了幾樣好菜來慶祝這個日子,在我的建議下,周老頭受邀同我們一起吃飯。他和老張的酒量很好,他們兩人喝光了兩瓶高粱酒,好像是喝啤酒一般;我只喝了兩杯葡萄酒,覺得已有醉意,八點鐘便去睡覺,在爆竹的響聲和人群的呼噪聲中酣然睡著了。
兩三天後,趙來到跟我一起吃中飯。他告訴我,我將要搬到紫禁城附近的一個新居,因為我不久就會要公開露面。
他說:「那是一幢小房,自成院落,是新式的。你現在就可以用新的位址寫信給你太太,那是南池子南灣子三號。我想,新的地方可以準備好給你在明天或者後天搬進去。你也可以寫信給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弟弟。」
自從上次寫信給我妻戴芬和我的弟弟凝瑞以後,到現在已經過了二十三個月以上。他們允許我恢復通信是來得那麼突然,我對這件事情簡直毫無準備。
「我應該在信裡向我太太說些什麼呢?」
「不要告訴我你不知道怎樣寫信給你太太。」趙微笑地這樣說。
「可是我上一次寫信給她到現在已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了。」
「你的家人很好,她們受到很好的照顧。你的年老的母親同過去一樣的健康。」
「我寫好這信後,是不是請你看看?你知道,為了我的未來計劃,我不想在信裡犯了任何的錯誤。」
「我們絕對的相信你。」趙露齒而笑。「我們覺不需要檢查你的信。好吧,你可以告訴她你已經完成了你的思想改造計劃,現在正在北平等待著新的職務。你可以向她暗示,你不久就可以看到她和家裡的人。」
他走了之後,我便坐下來寫信給戴芬和凝瑞,信裡措辭十分謹慎,在寄出之前,我把這些信送給趙檢查。
老張把我的信帶到趙的辦公廳去,趙馬上打電話給我,一邊大笑一邊說:「請你不要把你的信送給我檢查,這些信我不要看,由老張拿去寄好了。」
新的房子雖然比原來的小得多,但較為舒服。我有一個連著洗澡間的臥室,還有一個很寬的餐廳和客廳。老張和我一同搬進來,他並不怎樣快活,因為他的房間黑暗,沒有窗子,而且就在廚房的隔壁。
文昭也跟我同來,他用手指著沙發和其他的傢具,對我說,這些東西都是新添置的。我相信他的話,因為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甚至絲質的窗帷也是全新的。老張看到一套新的磁器杯碟和新的廚房用具,真是高興,像一個孩子般輕輕地觸摸這些東西。
文昭說:「我們要把這個地方收拾得整齊,因為你要在這裡招待你的親戚朋友。」他的語調並非毫無妒嫉和羡慕的意味。
稍後,他建議同我一起去買幾幅畫來裝飾新近粉飾過的牆壁。我們漫步附近的王府井大街──北平的皮卡得利廣場──買了兩幅刺繡的杭州西湖風景畫,掛在牆上。
我請文留下來吃晚飯,他同意了。他走了之後,老張興奮地在房裡踱來踱去,不斷對我說,我得到了局長級的待遇──有自己的住所,有特用的廚子和其他東西。
他若有所思地說:「公安部認為你是一個高級專家。事實上,局長也不會生活得更夠派頭。我說,主任,你跳得真快。」
第二天清早,趙寫了一張便條給我,說是「局長」要在當天來同我談話。我一等再等。「局長」終於在下午到來,他帶了四名隨員,包括趙和文在內。他戴上眼鏡,氣色不錯,是一個漂亮的人,年紀快到四十崴。
當我們握手的時候,他叫我「周先生」。
他說:「唔,我很久就想看你,可是蘇加諾總統來訪問和國慶日安全措施都由我來處理,因此我要到今天能夠來看你。」
我沒有甚麼適當的話好說,只好禮貌地點點頭。
「周先生,你經過了一段十分緊張的長時期思想鬥爭,我很高興你現在是一個新人了。不過,我要警告你,思想鬥爭是永無休止的。今天,你是澈底的改造過了,但這並不是說你永遠不再有任何的思想問題。要是你將來犯了錯誤,你不會再經歷同樣的步驟。黨和政府己經盡到了一切的力量來幫助你。人民的中國有著龐大的重建計劃,需要各種的工作人員。每一個人都有報國的機會,你也有。」
「我願由我未來的工作來證明我的忠誠和進步。」我裝出十分認真和誠懇的樣子。
「很好。我看過你的繙譯,譯得很好。也許還要你幫我們繙譯另外一本書」。然後,他轉向趙,接著說:「你注意好了。」
他向他的腕錶瞥了一眼,那是一個亞米茄牌金錶,然後突然站起身來,說:「我要走了,我很快就再來看你。還有,你在這裡舒服嗎?」
「的確十分舒服。事實上,我在這裡過著比在香港更舒服的生活。」
「假如你要什麼東西,告訴文昭好了。」
他和其他的人剛好離去後,老張喘著氣走進臥房來。
「你曉得,他是我們的局長,第一局的局長。在公安部裡面,羅部長把一切事情都交他辨。我不是告訴過你,他每天都去看毛主席呢。」
我想向老張打聽關於這位「局長」的進一步資料,可是為了慎重起見,我把說到嘴邊的話嚥下去。
趙在兩天後再來,給我一本《伏傑勒的審判》。
這本書是匈牙利出版的,內容是關於法庭指控伏傑勒充當美國間諜的紀錄。
趙說:「你從容的譯好了,這是一本很厚的書,但是我們不急於要譯本。」
我告訴他,我將在不超出三個星期的時間內繙譯完畢。
他說:「等一回,另外還有一個任務交給你。我們要你教我們的一些年青同事學英文,他們全是大學睪業生,但是他們在外國人的面前簡直不能說英語。」
「你要我開一班英文班嗎?」
「噢,不,他們個別來這裡接受私人教授。我相信在這種方式下,他們可以學得多些。」
「我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我希望先和學生們談談,讓我曉得他們的英文水準。」
趙表示同意,「當然可以。我叫文昭帶他們。」
當天下午,文帶了兩個年青共黨人員來看我。他介紹我們相識,男的姓喬,女的姓嚴。喬告訴,他是青島大學畢業生,嚴在北平外國語學校畢業。為了要知道他們的英語程度究竟怎樣,我開始用英語跟他們交談。在我看來,喬實在明瞭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嚴則時常不知所云。
在他們的要求下,我決定教喬讀蕭伯納的劇本,教嚴讀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除了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們每天上午都來。他們得到了上級的批准,可以在工作時間內來讀書。
我發覺他們都很用功,為了訓練他們的聽覺,我使用直接教學法,用簡單的英語提出關於書本內容的問題,並且鼓勵他們用英語來回答所有的問題。
不久之後,他們表示,除了在上午正常上課的時間外,他們希望在晚上也來看我,以便多獲實習會話的機會。他們急於求取進步,使我高興,我馬上表示同意。每一個星期裡,有兩三個晚上他們來看我,一直到接近午夜時才離去。
沒有多久,喬對我顯得那麼友好,幾乎每天晚上都來。他用英語結結巴巴地表示他對西洋文學的興趣;他並且告訴我,有一個時期,他被一個美國傳教士收養,但他已不再知道這傳教士的下落。他和我討論到政治以外的各種問題。晚上跟他在一起,使我頗為高興,因為我有了鬆弛的機會。可是老張不止一次向我表示了他對這種安排的不快,因為他失去了晚上跟我聊天的機會。
嚴是一個上海少女,在北平長大。二十歲剛出頭,顯得害羞和矜持。起先,她從來沒有在晚上單獨來看我,但從老張那裹知道了喬時常在晚飯後單獨前來,她也開始獨自來看我了。
她有一雙明亮的眸子,膚色很好,本身就很動人。她進來之前,總是在窗子上輕輕敲一下,問道:「周教授,我可以進來嗎?」我屢次要她不要再叫我做「教授」,但是她堅持這樣做,使我覺得不好意思。
她很安詳地坐在沙發上,留心聽我講話。有時候,我們在聊天,她就織線。她和喬比較起來,老張似乎喜歡和她在一起,每逢她來到的時候,老張總不會忘記給她倒一杯香片茶。一個晚上,他甚至冒著裂膚的寒風走出去買些冰冷的柿子來款待她。
後來我對他說:「老張,我可以看得出你比較更喜歡嚴,為甚麼呢?」
「嗯,」他抓一下頭。「你知道,我們這個地方像一個和尚廟,晚上有一個女同志跟我們在一道多好。」
「但是喬也是一個好人。」
「像你我一樣,他也是一個和尚(中國俗謂單身漢或跟妻子分居的男人之稱),此外,他每次擱得太久。」老張做了個鬼臉。
在那幾個星期裡,我埋首於書和繙譯工作,但有幾天晚上,趙叫嚴和喬跟我一起去看電影。我從不喜歡看蘇聯電影,在北平停留的期間內,我只看過一張英國電影,一張法國電影,和一張墨西哥電影。
有一次,嚴陪我去市體育館看蘇聯馬戲,雖然表現毫不精彩,但是有許多共黨要人到場觀看。在這種場合裡,他們的到場是被看作中蘇友好的象徵,同時也是一種政治任務。在中共區裡,甚至馬戲的觀眾也是事前經過安排和組織的。
到十一月底,我的弟弟凝瑞從哈爾濱寫信給我,說是希望來看我。我於是同趙商量,他建議我打電報給凝瑞,叫他立刻來北平。我這樣做了,兩天後凝瑞便來到。
我們在門口石階上互相擁抱,淚盈於睫,講不出話來。在過去兩年來,凝瑞曾經想盡辦法去探查我的下落,甚至向「最高法院」寄出請願書,請求給我公開審判。他深信我是無辜的,於是寫了公開信給「人民日報」,呼籲主持公道。自然他的信沒有一封給發表出來,「最高法院」也不理會他的請願。在絕望之餘,他去找我們的叔父周士觀。他是民主建國會的常務委員,建國會是共黨政權下的一個小黨派。我們的叔父一如大多數中共區的民主人士那樣膽小,他勸凝瑞不要管這件事情。可是凝瑞不死心,他繼續寫信給他所想得到的所有共黨領導人物,結果他遭遇了更多的失望。
其實,他在收到我的信前,早已從他的大學的黨委書記那裡曉得我已獲釋。黨書記在九月間召他去。向他說:「你的哥哥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你不久就可以收到他的音訊。」約莫在一星期後,我的信便寄到給他。
當凝瑞和我正在忙於談話時,老張走出去找文昭,去拿寢具和另外一張床。他回來的時候帶來趙科長的一張便條,告訴我應該和凝瑞自由地到處走動,以便消除他可能懷有的任何疑心。趙同時提議,稍後我可以介紹文、喬和嚴跟凝瑞相識,說他們是文化部的幹部。事實上,趙已叫我去拜訪我的朋友,他要文給我兩百塊「人民幣」,做為零用錢,並且給我一支門匙。
那天下午,趁著凝瑞在洗澡的時候,我去到和平旅館同趙略事交談,他再次告訴我,不許我向凝瑞透露任何事情,我應該恢復我的本來面目──無憂無慮和逍遙自在。
凝瑞的來訪使我停止了英文授課。那個姓嚴的少女由於太害羞,沒有繼續來上課,雖然到現在,她可以用英語和我交談而沒有多大的困難。在最初幾天,喬依然照常來,當我們讀著蕭伯納的《人與超人》的時候,凝瑞便留在臥室裡,潤飾他繙譯那本俄文和機械工程教科書的手稿。可是,有時他聽到喬對某些英文的奇怪發音,不禁吃吃地笑起來。這一定激怒了喬,他從此就不再來了。
由於我譯完了《付傑勒的審判》,我便把大部分的時間消磨於與凝瑞漫遊。我們馬上去東安市場,那是北平老居民最常去的地方,他們去買古董、珠寶、舊畫、字畫、食品和舊日常見的其他東西。我們一走進這個寬大地方的通道,便立刻感覺到完全變了樣,雖然這些通道的兩旁依然排列著各種攤位,攤位的主人臉上還是帶著同樣的北平式笑容,但是顧客的數目卻減至寥寥無幾了。大多數的人以羨慕的眼光看著那些物品和手工製品,可是沒有幾個人停下來買東西,他們甚至連價錢也不問。古董店亮著燈光,但看出沒有生意可做,店裡的助手把一雙手放進棉袍的袖管裡,藉以取暖,他們茫然凝視著空間,顯然對於這種被迫的悠閒感到厭倦。
走到那些舊書店的角落,我依然可以認出多年前在那裡買過許多心愛的書的一些舊書店。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我們走進其中的一家。我們的腳步聲驚醒了正在櫃檯後面打瞌睡的老頭兒,他擦著眼睛,以好奇的目光望著我們。我們好像來得那麼突然,他以不自然的微笑來跟我們打招呼。這家店子一向出售英文、法文和德文書的,有一個時期,它的顧客全是教授和學者,這些人如今只能以俄文書和共黨的文獻來滿足自己了。在滿佈灰塵的書架上,我發覺有莎士比亞、喬叟、密爾頓、海涅、歌德、福樓拜、莫泊桑和但丁等人的著作,但看到一本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奮鬥》,使我吃了一驚。這本書是新的,給放在其他古典名著中。
「你也可以賣這本書嗎?」我指著《我的奮鬥》。
他遲疑地說:「唔,事實是自從解放以後我們就沒有一個顧客了。此外,文化部的幹部沒有告訴我們,哪些書是禁書。」
凝瑞和我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因為我們都十分明白,大多數的共黨幹部不懂外國語文。
「既然沒有顧客,為什麼你不把店關掉?」
「為了市場的繁榮,我們奉到命令要繼續做生意。」這個老人嘆息一聲。「誰要結束他的生意,就得呈遞請願書,研究和批准是很費時的。」
聽了他那淒涼的語調,我想買一兩本書來給他們打打氣。然而我充滿好意的企圖結果不能實現,因為凝瑞比我更加慎重,他敦促我馬上離開。
在另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們來到北平購物中心王府井大街,當我們經過「北京百貨公司」的門前,我拉凝瑞走進去看看。這是最大規模的一間百貨公司,是商業部經營的,新蓋的大廈共有五層,髹上灰色,形狀像一個火柴盒,裡面沒有升降機,我們要徒步「遊歷」。
各個部門看來井井有條,年輕的男女店員店員都穿著潔淨無瑕的人民裝,像子穿梭般在櫃檯和窗櫥後面走動。不過,這裡也是參觀的人多過真正買東西的人。在頂樓,我們發現了進口貨物部,窗櫥陳列著瑞士手錶,包括有勞力士牌和亞米茄牌,還有像萊卡牌和康塔斯牌的德國照相機,此外還有英國的西裝衣料和美國的皮鞋。看一看標價,不禁使我吃了一驚,一個自動上鏈的勞力士手錶取價大約人民幣一千元(超過一百五十英鎊),一個萊卡牌照相機值人民幣三千元。不消說,這些東西遠非一般老百姓的購買力所能負擔,這些人的平均每個月收入尚不足八十元。等到一些蘇聯的顧客來到,這個謎才給解開。他們從口袋裡拿出一束一束的新的人民幣,來購買手錶和照相機,以便滿足他們的購物慾,對於我們來說,金錢好像是毫無意義的東西。在中共區裡,他們的生活和行動的確像無產階級的王子和公主一般。
我感到厭惡,立刻和凝瑞離開這家商店。街上的寒氣冷卻了我的憤怒,但我們都不想繼續漫遊。
凝瑞離去的兩三日後,趙陪著一個姓李的局長來我住所看我,同李一道來的,還有一個名叫田海山的年輕共黨人員。李是一個說話柔和的北方人,在講話的時候不斷地微笑。他告訴我,北平大公報社長王芸生把費彝民從香港寄去的一封信轉給他,費在信裡歡迎我重回香港大公報工作。
我立即告訴他,我寧願留在北平工作。我之所以這樣說,首先是因為我不能確知那些共黨人員是否說真話;其次,我討厭看到費彝民和他那一般人。我想,假若我留在北平,我至少可以不會再遭遇到麻煩。我知道我在中共區是不會快樂的,但當時,我覺得我不能重返香港的大公報工作。那個時候,我的心情是有點聽天由命。
李局長望著我,說:「但是我們以為你應該回香港去,自然你在北京也是有用的,要是我們仔細的估量每一個因素,你重返你的老崗位將會好的多。第一、大公報需要能幹的人;第二、我們答應過,你在思想改造之後就回到香港去;第三、我們要擴大我們在香港的國際統戰,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像你這樣的一個人在那裡將會對我們大有幫助。你有許多外國朋友,你把他們爭取過來成為人民中國的朋友並非沒有可能。還有,你可以做我們的耳目,探聽許多西方對我們的反應。」
我立時明白讓的真正計劃,是要把我逐漸變成一個共黨特務,我自然起了反感。
他繼續說:「老實說,你為M工作已經對人民很有害處,現在是要求你同樣做出為人民服務的時候了,你不要害怕,因為在香港沒有人知道你在過去幾年來發生過甚麼事情。你的外國朋友對你不會有絲毫的懷疑。要是你在香港執行工作的時候限於危險,你有一個有力的政府和一個大國來支持你,你永遠不會孤獨。香港的英國政府不敢做任何於我們不利的事情,那我是有把握的。」
趙和田焦急地望著我。
過了一會,我說:「假如黨和政府決定我應該回香港去,我只能服從。但是我對於我在國際統戰所擔任的任務還不大清楚,我需要接受領導以免犯有錯誤。」
「好,」李拍著我的肩膀。「你有了一個正確的決定,你不要為了回香港而擔心,我們的最好的戰士永遠是從矛盾和鬥爭之中訓練出來的。我們不會要你馬上在香港擔任甚麼工作,我們可以等待。現在,我們得談到別的事情。噢,我們已經決定,你應該在舊曆新年以前回到香港去。為了加強你的愛國心和對社會主義未來的信心,你和老田將要到東北去旅行一次,參觀一些工廠、礦場和農場。你可以看到大多數外國遊客不許看的東西。甚至費彝民也沒有你看得那麼多。」
「我幾時去東北呢?」我感到興奮,想著可以再有機會看到凝瑞。
李轉向那個高而年輕的共黨人員,「老田,旅行的準備怎麼樣?」
「局長同志,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可以照你的意思隨時動身去東北。依照原來的計劃,我們將要訪問瀋陽、撫順、鞍山、長春和哈爾濱。我們大概要費時八九天。」
「好,我可以讓你來決定動身的日期。今天晚上,讓我們到全聚德吃飯吧。老周回香港去以前,應該嚐嚐北京烤鴨。」
全聚德是吃烤鴨的最好的地方,但是,不是許多人都能夠在那裡吃得到的。由於填鴨有限,只有政府官員和外交人員才有一嚐美味的優先權。只不過在幾天之前,我曾經和凝瑞來到這個地方,可是卻吃不到鴨子。
這一天的晚上,情形完全不同。侍者有禮貌地帶外面走進一個預先訂好的房間,房裡修飾得彩色繽紛。鴨子味道真好,比我們在香港吃到的好得多。把鴨子一片一片的切開,是需要高度技巧的。在過去的日子裡,我只看見男人做這個工作,但這一次,我卻看到兩個年輕的女子切鴨,使我不勝詫異。她們對這個工作是很能勝任的。
在吃晚飯的時候,李從頭到尾高談闊論,講著笑話,並且告訴我們關於毛澤東的軼事。像大多數共黨人員一樣,他把毛稱做「主席」,而不提他的姓。周恩來被稱做「總理」,劉少奇被人親切地叫「少奇」。這給我以一個印象,認為共黨人員以宗教的敬畏心理來崇拜毛澤東;對周恩來表示高度崇敬;認為劉少奇是十分接近他們的人。李告訴我幾個關於「主席」的故事,發覺我在津津有味地聆聽,他表示喜悅。
「你回到香港以後不許寫這些軼事。主席和西方的領袖不同,他不喜歡宣揚。在長遠看來,宣傳將會造成個人崇拜,他只有做人民的一份子。」
趙插嘴說:「這是一個偉大領袖的偉大之處。」
李突然說:「我們都看過你的《侍衛官雜記》,寫得很好,全是事實。前幾天,我看到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同志和全國作家協會秘書長劉白羽同志,他們都很推崇你這部書。」
他那出乎意料的讚許,使我覺得不好意思,我想法子說出了幾句謙遜的話,以表示我的感激。
當我們分手的時候,已經將近九點鐘了,我堅持步行回家,因為我在吃飽飲醉之餘,需要吸點新鮮空氣。
在樹影之下漫步,我沉溺於默想中。共黨對我的態度一如過去那樣的令人費解。看來他們的確相信,他們改造了我──一個「帝國主義者的特務」──已經獲得成功。他們是否深深地相信,我將會在香港為他們做間諜,來表示我感激他們對我的寬大呢?自然他們沒有想到我編造了關於我自己的荒誕故事,來滿足他們的虛榮心。對他們來說,我是一個「經他們澈底改造過的真正特務」。假若我是他們所想像的「真正特務」,我會被他們的大度和寬厚所影響。可是我自始即受誣害,他們對我所做的事情,在我看來,那是滑稽可笑的,甚至是荒唐的。我知道我是要報復的,這個日子似乎越來越近了。
第二天上午,田約莫在十點鐘來看我。他表示我們將在三四天後動身去東北,然後他告訴我,組織已經決定給我買一件皮大衣,使我在這次旅行中抵擋東北的嚴寒天氣。我為了要表示客氣,於是告訴他,買一件羊皮大衣就已經夠好了,因為我不想組織花太多錢。
然而田馬上向我表示,他已接到命令,給我買一件銀狐大衣或者貂皮大衣,當我回到香港的時候,可以當作一件很好的紀念品。隨後,我們便是去前門地區的一條橫街買大衣。那是一條十分狹窄的街道,北平的大多數皮貨店都可以在這條街找到。我們從一家店到另一家,走過不下十多家,終於選了一件貂皮裡的藍色大衣,價值人民幣四百元(略高於六十英鎊)。田依然想買一件比較貴的,但我堅持要這一件,因為我想到日後可以把它改成一件貂皮大衣給戴芬穿。
以後,我們去王府井大街的「北京百貨公司」買了一套海藍色蘇格蘭呢制服,一頂皮帽,一些羊毛內衣和羊毛襪子。田再次堅持要給我買最好的東西。
